语言哲学观论文优选九篇

语言哲学观论文第1篇
赵奎英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おお
赵奎英教授的著作《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从统观中西语言哲学的高度,对中西诗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比较分析,内容宏富、体系完备,并且针对语言诗学中的盲区和难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诸多学术难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提出了诸如广义的“语言诗学”;“名”与“逻各斯”的比较框架;中国古代的“名”言观和“无名本体论”;西方传统的“逻各斯语言观”和“逻各斯本体论”;“有韵的逻各斯”与西方传统的“纯诗学”,“有象的道”与中国古代的“大诗学”;中国古代诗学文化具有“空间化与诗化”特质等一系列富有洞见的论题。这又使得这部厚重之作充满了理论创新的锐气。而在诸多的突破与创新中,该著作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开辟的新领域、提供的新视野、确立的新框架尤应被提及。
赵奎英著作以最广义的“语言哲学”和“语言诗学”作为理论起点,重构了语言哲学与诗学一贯的源始关联性,确立了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中的语言诗学领域和语言哲学视角。该著作指出,一提到“语言诗学”人们往往会联想到20世纪西方的俄国形式主义,并且与此后兴起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流派联系在一起。但这些只是伴随着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出现的“狭义上”或“较广意义上”的语言诗学。语言哲学与诗学的本然关系要远远早于20世纪西方文论对语言产生普遍的兴趣,对于语言观念与文学观念内在关联性的关注,在中外文论史上自古就有。由于文学本来就是一种“语言事实”,人们的语言观总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们的文学观,语言哲学总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文学的生成运思方式。因此那种最广义的“语言诗学”,亦即那种“受到某种语言哲学观念或语言学研究状况影响的、从语言角度切入文学研究的文学理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文学理论史上一直都是存在的。一提到“语言哲学”,人们也容易想到英美分析哲学这种最狭义的语言哲学,但这里的语言哲学同样是在最广义上使用的,它泛指“一切从哲学的角度思考、研究或关注语言的普遍性质或一般问题的哲学和一切从语言学的角度关注或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语言学”。这种最广义上的语言哲学观念潜含于文化的最根基之处,通过它可以更清晰地确定诗学研究最基本的命题,透视中西诗学精神传统的生成特质。但这种广义的“语言哲学”和最广义的“语言诗学”在当前学界的研究中都是相对地被忽视的。而赵奎英教授的著作正是选取最广义的语言诗学作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领域,并以最广义的语言哲学的两大基本问题作为透视角度,对中西语言诗学的基本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比较分析。这种理论旨向决定了此书博大厚重的研究风格。
宏大的理论视野是以对传统理论的重估为前提的,正本清源的理论梳理必然带来理论的创新。在中西文化比较平台的界定上,“道”与“逻各斯”因其代表了中西哲学的最高本体,长期以来成为中西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比较哲学的基本框架。学界虽有极少数的对这一框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批判质疑,但这一框架的流行性、统治性地位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真正被撼动。该著作对这种几成定势的比较框架进行了一次更彻底的检视,它通过“名与逻各斯”和“道与逻各斯”的重重对比,让人们看到“名与逻各斯”实际上比“道与逻各斯”更适合做中西哲学、诗学、文化比较的基点和框架。该著作指出,“逻各斯”是西方哲学文化的基点,西方传统最初正是以逻各斯领会语言的,也是视逻各斯为最高本体的。西方传统的语言观是一种“逻各斯语言观”,西方传统的本体论是一种“逻各斯本体论”。“逻各斯”亲近“理性”、肯定“逻辑”,是“言说”性的本体,逻各斯语言观和逻各斯本体论共同为西方传统诗学的生成提供直接的语言学依据。而“道”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本体,它混成无形、无极无分,是一种“非名言性”的无名本体。“道”与“逻各斯”虽在本体地位上具有相似性,但相异大于相通,很难建立合理的对话关系。相反,被以儒家为代表的各家推崇为“天地之纲”、“圣人之符”的“名”则与“逻各斯”更具有可比性。“名”渗透于中国古代的语言学、逻辑学与政治伦理学中,具有“概念名称”、“书写文字”以及“名分名誉”的含义。中国古代的语言观是一种“名”言观,中国古代的逻辑学是一种“名”学,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学则与一种“名分”之学难解难分地纠结在一起。“名”对于中国诗学传统以至整个文化传统的生成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如果说“逻各斯中心”与“反逻各斯中心”构成西方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古代语言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则是围绕着“名”与“无名(道)”展开的。“名”与“逻各斯”堪称中西诗学文化精神生成的基点性依据。但同样作为中国哲学文化基点的“名”却长期被掩盖于“道”的光辉之下。“道”与“逻各斯”比较框架的确立,更使“名”对于中国诗学、文化生成所具有的基点性意义得不到有效梳理。而赵奎英著作重新厘定中西诗学比较的平台,把“名”与“逻各斯”作为中西语言哲学、诗学比较研究的框架,在中西文论比较研究上也因此具有重要的突破性意义。
把“名”与“逻各斯”作为中西语言哲学、诗学比较研究的框架,并不是要排斥“道”与“逻各斯”。赵奎英明确指出:道家之“道”排斥“名”,但以儒家为代表的各家所尊崇的“名”却向往着“道”。因此,以“名”与逻各斯作为比较的基点和框架,并不会把“道”排除在外,而是要把“名与道”同时纳入视野,在对“名与逻各斯”、“道与逻各斯”、“名道(无名)悖反”与“逻各斯中心”的同异比较中,说明它们对于中西诗学精神生成的复杂意义。由此可以看出,“名”与“逻各斯”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框架,以此为基点,更有利于揭示中国传统诗学精神的整体风貌和诗学结构的复杂格局。
语言哲学观论文第2篇
关键词:语言哲学;孔子;《论语》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2-0136-02
一、语言哲学简介
20世纪是语言哲学转向时期,人类关于哲学的思索由本体论、认识论转向了语言,“转向”带来的不仅是新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在哲学观上的革命性转变。语言哲学在此时崛起,成为该时代科学的主流。关于“语言哲学”的概念,众说纷纭。不同的哲学流派以不同的方式研究语言,因此得到的结论也存在差异。语言哲学研究包括对语与句的分析,对言语行为的探讨,对意义、指称与真理理论的研究,对语言与心理、语言与思想、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等研究。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主要分为两大流派:英美语言哲学和欧洲大陆语言哲学。英美语言哲学主要运用语言分析方法对语言的意义理论、真理理论进行分析和论述。欧洲大陆语言哲学更注重语言的结构、功能和语言的人文特性。但这种分析只是从宏观上比较粗略的区分,事实上两派中的语言哲学家在研究内容与方法上有相互借鉴交融之处。在英美语言哲学内部根据研究方法的不同,分为逻辑分析学派与日常语言分析两个学派。逻辑分析学派的罗素主张指称理论,同时根据亲知原则,强调了亲知在真理断定中的重要性。前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等著作中提出图像论及逻辑原子论的符合论,他认为名称和对象是逻辑上的对应关系,命题甚至整个语言结构也与客观世界在逻辑上是对应或同构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语言是世界的图像。日常语言学派采取概念性的日常语言的分析方法,对日常语言进行精细的分析研究。从摩尔、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到塞尔形成了包括言语行为理论的一整套有影响力且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与此同时,也有不少语言哲学的研究者将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生成语言学归为语言哲学的一个分支。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语言哲学有着比较纷繁复杂的流派传统,而且各流派之间观点不同,甚至有着较深的矛盾。本文在此将西方语言哲学与《论语》中出现的关于语言的哲学性思考进行分析探讨,希望借此对我国儒家经典著作《论语》及该时代的语言哲学思想有较为深入的挖掘。
二、语言哲学的真理观
真理“符合论”是真理观中最古老,也是发展得最为完整、深入的理论。一开始“真理”便与语言联系在一起。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根据前人的观点指出:同一事物不可能具有一对相反的性质,不存在“一个事物既是白的又不是白的”这种现象,因此对事物的陈述也不能有居间状态,“对立的陈述不能同时为真”,“对于一事物必须要么肯定要么否定其某一方面”。所以对于追求真理的人来说,“说存在者不存在或不存在者存在的人为假;说存在者存在和不存在者不存在的人则为真”。“说”在这里不仅仅是“陈述”,更是以言语形式所作的判断。
亚里士多德的真理判断标准:与事实符合,它们则为真,是真理;与事实不符,则为假,不属于真理。这种真理观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内涵,他承认在人这一主体之外,客观的对象世界的存在。亚里士多德的“符合论”通常被学者认为是传统经验主义真理观的代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中涉及的“世界、实体”非柏拉图式的理念实体,而是人们可以由感官感知到的“质料”与“形式”都相同一的具体事物,他认为真正的真理乃是主体认识与客观世界的一致。
罗素是真理符合论的代表者,他和维特根斯坦一样,主张真理是逻辑上的符合。他认为传统的符合论是认识论上的符合,真理就是要求命题与人们所获得的经验相一致,虽然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存在但人类却无法经验到的事实,是无法根据这个理论得出其真理性的。因此,他主张逻辑原子论,即从逻辑的角度认为命题与事实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同构关系。
除真理符合论外,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与真理融贯论也是比较有影响的真理理论。实用主义真理观并非“有用即真理”那么简单,包括有用的概念才是真的概念,即概念的意义在于它的用途等较为深入的论述。真理融贯论事实上是受到黑格尔的整体主义本体论的影响而产生的。真理融贯论把真理理解为命题之间、判断之间、信念之间的融贯性。在一个理论中,如果一个命题与其他命题相融贯,这个命题就是真命题。
三、《论语》中的真理观
语言哲学观论文第3篇
1.1关注语言起作用的条件
语言哲学对语言起作用的条件也很关注。除了经典的格赖斯的合作准则,其他的如马克主义语言哲学、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以及认知语言学等对此都有论述。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关注语言起作用的社会阶级背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描述交际中的语言合理性,认知语言学关注语言背后的人的认知机制。可以说,语言哲学是从社会条件、交际条件和认知条件等多个角度分析了促使语言起作用的各种因素。翻译研究对促成翻译语言形成的各种条件也很关注。例如,翻译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研究就突出了社会条件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以及翻译对社会条件的反向作用。再如,译者个人条件的研究也日趋系统化,形成了以翻译能力为突出特点的多样性研究。例如,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学科能力、文化能力和转换能力(Neubert2000:3-18),还包含两种语言的交际能力、超语言能力、工具—职业能力、心理—生理能力和策略能力(Orozco2000:199-214)。此外,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理解文本时其自身条件和状况也很重要,例如翻译过程中控制干扰的能力如何,重新表述的能力和执行翻译任务的能力如何。这些因素对形成翻译的语言也很关键。
1.2关注意义、心智与语言之间的关系
语言哲学研究包含了很多关于个体心智意义与环境意义之间的互动形式。意义意味着有意识的经验,但是只有通过介质来理解的经验才能算作意义。在现实世界中,最基本的介质是实体,例如茶杯或者椅子,与一定类型的经验有关。在这种最简单的情况下,意义成为生命形式中物体角色的副产品。随着符号的兴起,意义需要获得与其介质相关的独立地位。在人类的语言中,这种地位得到最复杂的表现。随着语言的发展,人类的生命形式开始独立于意义的集体认知,而这反过来又引起了物体意义的激增。例如,Searle对社会现实的定义是内置于个体心智中的“我们意识”,而Croft认为意义是在言者大脑中发生的事情。与此相比,Hart是把个体放在意义产生的身体和来自外部世界的意义之间的接口上。这些是社会认知语言学通过意义增值来实现语言功能的方式。翻译研究一直以来也关注意义、心智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早期的“意对意”翻译还只是研究的雏形,稍后,雅各布森的语言意义与对等的本质进一步突显意义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后来,哈蒂姆和梅森的语境和语篇研究也关注到翻译中的意符层次。当代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更是将意义、心智与语言之间的关注在翻译过程中的显现描述得非常深入。这些认知形式对翻译研究的促进作用已经得到研究者论证(参见王寅2008:211-218;谭业升2009:36-58)。
1.3关注实现语言功能时的语境约束
语言哲学对语境研究非常关注。维特根茨坦关于意义的研究都没有离开语境的分析,连他提出的“激进翻译”也是一种在语境约束情况下的意义建构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将语境约束突显为社会语境,在语言的阶级性上建构理论。言语行为理论也非常关注语言所起作用的语境,即必须从语境中概括和抽象使其成为语境类型,从言语行为中概括和抽象使其成为语言行为类型。换言之,语言与语境约束之间的关系又被视为一种语境化、实例化的语用行为。它是一种特殊的语用行为,是语言内之意和语言外之意的混合。话语环境在交际中起着决定作用,它促使言说者的话语转化成一个或另一个语用行为。言语的内容只是交流意义中的几个因素之一。翻译研究对语境的约束更为敏感。翻译依赖于两个相互分离的因素:语境效果和加工努力。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境的互动体现为双重特征。译者既能够在语境重建过程中发挥主动作用,也受到语境约束的影响。就语言内部的语境因素来看,韩礼德把语境分析分成三个方面:语场、语旨、语式。豪斯在韩礼德的语境分析三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译文评估模式,扩大并细化了语境约束的特点,贝克也在韩礼德模式基础上将其应用于语用概念,对翻译中的语境推理与约束也做了深入分析。这些研究都显示了从选词的微观层次到篇章的建构层次乃至译文之后的社会文化意义都与语境约束相关。
2.语言哲学与翻译研究的差异
虽然同样关注使用中的语言,由于学科理论建构基础不同和研究侧重点影响,语言哲学与翻译研究的差异也很明显。首先,语言哲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翻译研究不具备,即语言哲学对语言的真值条件非常关注。就客观语义学来看,其中认知主义的客观语义学就包括真值对应论和真值条件论。真值对应论始于Frege,认为“有一个独立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客观外在世界,语义是客观世界的内在表征,来自与所指的客观范畴密切对应的关系,因而注重描述语句与环境是如何匹配的”(王寅2006:268)。真值条件论是由Tarski、Davidson等提出的,“他们更强调‘真值条件’,句子的真值条件就是决定句子真假所依赖的客观事实。句子的客观意义是由使得该句子成真或成假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若能确定所说话语赖以成真或成假的条件,也就能理解句子的意义”(王寅2006:271)。此外,在言语行为理论和格赖斯的语用传统中,对语境因素的强调同样重要。语用参照的结果体现在言语真值内容中,而这样的语用扩大或调解在建立言语意义方面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语用参照的主要成分包括:非语言意义,直观的真值条件,组成成分的验证(Jaszczolt2010:2898-2909)。其次,语言哲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而翻译不具备的,即语言哲学强调“元语言”、“言语”、“话语”、描述空间和时间体验并做出一定的逻辑判断。格赖斯的“会话与含义”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都与话语有关。认知语言学对语言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体验描写更为深入,将语言的“时”、“体”概念与人的认知体验相结合。语言哲学都关注言语行为的推理与分析,并对此做出一定的逻辑判断和理据验证。第三,与语言哲学相比,翻译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更加关注双语环境中语言间的转换情况,例如语言的对应与对等模式,语言对的转换与迁移模式,语篇的多重关系网络等等。翻译研究强调“原作者”、“源语言”、“译者”、“译入语”,它以语言对比为前提,涵盖了文体学、文学理论、文化研究、交际理论、语言哲学、普通语言学、机器翻译、人工智能、对比语言学、语用学和语篇分析等多个领域。翻译研究关注原文语言在译文中的变化,描述双语空间中语言的转化情况,并对其中的线性和非线性变化做出分析和评价。以话语和语篇连贯为例,语言哲学认为连贯与衔接是意义产生的基础,语言学意义上的连贯可以分为组合连贯与聚合连贯,局部连贯与总体连贯,有标记连贯与无标记连贯。与此不同,“翻译上的连贯是个多重关系网络,可以分为不连贯、伪连贯和互文连贯”(王东风2009:47-55)。第四,语言哲学与翻译研究有不同的语境分析路径。在语言哲学中,语境的概念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语用的定义通常与语境的含义相关。因此,Stalnaker(1999:43)认为“句法研究句子,语意研究命题,语用研究语言行为及其表现于其中的语境”。Levinson(1983:32)也认为语用学是一种将语境考虑在内来理解语言的理论。在语用学中,研究者关注意境及其所代表的内容之间是如何互动的,所使用的语言表述与语境是如何相关的。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能力被概念化为一种语境化再现过程。因为在翻译过程中,语言的延伸不仅在一种新语言中给出了一个新的形式,而且是从早期的原语境中提取出来放置在一个新的语境中,同时伴有来自交际传统、类型与读者期望范式的不同价值。总之,语言哲学关注意义生成的过程、逻辑推理过程以及相关语境,而翻译研究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关注语言之间的转换和语境重建。
3.经典哲学对翻译研究的促进
经典哲学对翻译研究具有推动和促进的积极作用。早在2000年,英国翻译理论家芒迪在《翻译学导论》一书中就专门写了一章,定名为“翻译的哲学研究”,收入了斯坦纳的阐释步骤、庞德与语言的能量、本雅明之译者的任务和解构主义等内容。后来,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主编的《翻译研究读本》也收入了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将其作为从哲学途径来研究翻译的主要内容。2007年,我国学者单继刚所写的《翻译的哲学方面》是对经典哲学与翻译研究之间关系的较为全面的总结,包含了解释学、解构论、分析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方面。总结目前经典哲学对翻译研究的促进作用,笔者认为可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促进了翻译研究从语言操作的微观层面上升到语言世界观的研究。早期的翻译研究特别是语文学阶段的翻译研究对于语言的微观层面非常关注。例如,早期西方“字对字”还是“意对意”的翻译,我国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等,都对于翻译的语言风格和翻译策略模式有了初步的讨论。后来,语言学阶段的翻译研究其模式扩大到语言意义与对等的本质,并对翻译过程中语言的转换迁移模式做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哲学视角的翻译研究进一步将翻译研究的框架扩大到语言世界观层面。例如,翻译的本体论研究使得翻译的本质研究和翻译主体性研究打开了语言世界观的大门;阐释学的翻译哲学观更进一步,认为“作为实践哲学对话,翻译是两种世界观的融合,是人类走向‘交谈共同体’的必由之路”(单继刚2007:38)。斯坦纳则用了四步原则描述语言与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并指出“一切理解皆是翻译”。这不仅扩大了翻译行为的范围,而且进一步推动了翻译研究与语言世界观的融合。格赖斯的经典会话原则更是将翻译研究中的话语意义与逻辑推理结合在一起。此外,解构主义进一步为翻译的不确定性研究提供了哲学视野。如果说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所描述的译作是原作的“afterlife”,这是具有解构意义的初步阐释,那么德里达的“在场”、“延异”、“播撒”等则是对此作了进一步深入的哲学阐释,这与奎因的翻译的不确定性相呼应,促进了文本层面的翻译研究向语言世界观研究的进一步转化。第二,促进了翻译研究从语言上升到语义再上升到语用。翻译研究离不开语言研究,随着跨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翻译研究也从早期的语言形式研究(例如,词汇层、短语层、句子层、语篇层)逐渐走向深入的语义研究。例如,翻译中的意义如何再现,语境参数对其影响如何,翻译过程中的心智意向性如何体现,翻译中的准确价值、绝对价值和默认价值又该如何体现以及相关语义学对翻译的深度影响如何等等,而真值语义学则进一步促进了翻译中合并再现的认知原则。随着实践哲学的发展和促进,引导翻译研究回归生活世界的语用理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李菁的研究表明:“基于言语行为理论、规范语用学和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交往实践语言观,应是实现翻译研究语用学转向的一条合理的理论途径”(2009:256)。李菁的研究还进一步分析了言语行为理论中的语旨力、意向性、构成规则与协调规则以及语境等概念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规范语用学对翻译活动的重新定位,言语的双重结构对翻译文本意义理解的制约以及言语行为有效性对重建翻译活动理性的指导作用等,对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转向做了充分描述。第三,促进了翻译研究走向心智认知深层结构。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认知哲学也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认知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新趋向”(侯敏2012:1)。“认知哲学采取语境实在论立场,奉行语境纲领,是一种区别于传统认知论的新认识论和方法论,主张认知现象是语境依赖、语境敏感和语境限制的”(侯敏2012:3)。认知哲学研究语言的具体途径是通过几个有限的人类的认知方式对语言现象做出统一的解释。将认知哲学引入翻译研究不仅对翻译现象进行了解释,也对翻译语言背后的认知机制作出了解释。从理论上来看,概念隐喻翻译观、概念整合翻译观、关联翻译观、原型范畴翻译观、框架语义学翻译观以及翻译认知心理学等不断向前推进和发展,丰富了翻译研究走向心智认知深层结构的理论基础。从实证研究来看,研究者采用各种不同方法、使用不同工具来验证多样化的翻译过程,涉及到翻译时间、翻译阶段、翻译问题的解决方式、翻译策略的选择路径以及不同翻译背景译者的翻译心理机制比较,主要研究方法涉及有声思维、对话协议、键盘录入和眼动研究等,其结果都为翻译研究走向心智认知的深层结构提供了理据。
4.结语
语言哲学观论文第4篇
摘要:乔姆斯基创立的“转换生成语法”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乔姆斯基革命”。乔姆斯基对语言使用的创造性的论述,有效地解释了各种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产生的语言哲学根源。这场革命之所以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乔姆斯基把哲学思考引入语言学研究,对语言问题进行深刻哲学思考和探索的结果,在这种探索的背后蕴藏着其独特的哲学含义,从而也使得他的语言理论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同时,乔姆斯基语言哲学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继承和留存。研究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特质,对于当前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乔姆斯基;语言哲学;马克思语言哲学;当代论域
中图分类号:H0-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6-0128-05
一、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溯源
研究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根源,不得不提到维特根斯坦和洪堡特两个人,这两人对于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影响至关重要,另外,还有笛卡尔与皮尔士等人。乔姆斯基与洪堡特在诸多方面一脉相承,乔姆斯基继承并发展了洪堡特的语言哲学思想。洪堡特是19世纪德国最负盛名的语言学家之一,他提出了“语言内部形式”的概念,它实际上指一种语言的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系统。他认为这种结构系统深藏在语言内部,是每一种语言的独特属性,应该是语言研究的真正对象。[1]洪堡特认为每一种语言就其内在形式而言,包藏着一种确定的世界观。语言是思维不可或缺的伴行者,也是思想的手段。理解语言内部形式,是某一语言共同体特殊统觉形式与语言外部形式相互关系的总和以及由此产生的语言自身的客观规律,包括该语言的词源进化过程。在划分一般感知时出现的不同词类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语言内部形式存在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对不同物体、活动、质量和状态的划分为语言进一步形成直接提供依据。洪堡特的这种语言世界观和语言的创造性特征对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产生了巨大影响。洪堡特于19世纪初即提出语言能力这一观点,乔姆斯基继承并发展了其理论,并借鉴了皮尔士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中的两个重要的思想后(即猜测本能和溯因逻辑),提出了他的“天赋说”。乔姆斯基的“天赋说”认为,人具有天赋的语言能力。乔姆斯基的语言天赋假设建立在他对一些重要现象的观察之上,而这些现象绝不可能用其他方式做出正确的选择。乔姆斯基对洪堡特语言哲学理论的继承以及自己的理论创新,使得乔姆斯基对语言使用提出了创造性的论述,有效地解释了各种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产生的语言哲学根源。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使用的创造性使人们借助有限的语言手段不断生成无限个新的表达式,新的思想伴随这些新的表达式而产生,使我们得以用新的语言和视角来谈论和理解世界并改造世界,满足我们对独创性的心智需要。乔姆斯基还认为语言的命题意向与命题之间的组合就是人(命题意向主体)在理解、诠释自身;每一个人都站在世界之中,用时代和世界赋予他的全部知识与对时代和世界的全部理解来解释自己。人在世界之中,同时又通过世界来理解其自身。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亦受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影响,二者从两个不同层次对语言进行思考。他们对语言基本属性的阐述角度和侧重点是有差异的。站在语言哲学的高度,他们能宏观地捕获语言的基本特质并进行科学分析。维特根斯坦与乔姆斯基在对语言的关注和认识上有交叉、相似或者完全不同的观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批判日常语言,追求理想语言;后期则通过回归日常语言的方式继续对语言的反思。表面看来,前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是针锋相对的,但实际上它们却统一于“语言批判”。[2]作为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基点,语言批判是他终其一生的追求。随着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研究的不断深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点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对哲学的重新理解可以说是哲学史上和哲学观点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其核心思想就是“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只有在使用中才有意义,词语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分析,从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来加以论述。这对于后来的语言哲学,尤其是日常语言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不仅影响了日常语言哲学,而且对语言学也有很深的影响。他认为“语言既是结构严谨、自组织性极强的、相对自足的简单系统,又是与多个相邻系统交互影响和作用的复杂系统”,[3]他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直接导致了日常语言学派的产生,也直接促成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诞生。1957年出版的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是“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构建开始的标志,同时也拉开了第三次语言哲学转向的“认知革命”的序幕。在《句法结构》中,乔姆斯基开始关注人脑的形式属性和普遍语法,注重语言哲学理论的构建,强调语言哲学及语言的解释性,采用假说―演绎性的理论方法,开创了全新的语言哲学研究视角。[4]
乔姆斯基明言其语言哲学思想是对皮尔士语言哲学思想的继承,乔姆斯基语言“天赋论”的哲学基础主要来源于皮尔士,乔姆斯基语言习得理论的哲学背景是皮尔士一般知识获得体系。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天赋思想借鉴了皮尔士认识论的两个重要思想:猜测本能和溯因逻辑。乔姆斯基语言习得模型中融合皮尔士的认识论(溯因逻辑)思想,在猜测本能基础上的溯因―演绎―归纳的知识获得过程,即儿童从有限素材基础上本能地利用溯因推理建立假设和理论,创造性地演绎生成新语言事实,再由归纳在经验中检验这些新语言事实,从而获得语言知识。这是乔姆斯基首次把哲学融入语言的概念里,对语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使得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哲学范畴和哲学意义。
二、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思想内涵
语言哲学具有母哲学的性质,同时,语言哲学也是分析哲学的一个分支。分析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之一,它的主要方法论和基本理论突出地表现为经验主义的哲学主张。现代哲学的分析方法与现代逻辑密切相关,而现代逻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注重语言的逻辑句法。这是一个从语形到语义的分析过程,也就是说,是通过对语言结构的逻辑分析进入对语言意义的研究,或者说,是以语义分析作为出发点而展开的对语言结构的研究。分析哲学的发展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色就是“语言的哲学转向”,通过对语言的基础问题的分析展开哲学讨论。语言的哲学转向有双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20世纪初发生的从自然语言到理想语言的转向,其结果是分析哲学的诞生;第二种含义是战后发生的从理想语言回归于自然语言的转向,其结果是语言哲学的诞生。分析哲学从经验主义到唯理主义的转变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其中的典型标志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一定的语言观点或者理念就决定了一定的哲学思考范式。
乔姆斯基通过对语言机能的先天性和语言使用的创造性研究,清楚地认识到人的本质特征和自由的重要性。[5]他认为,自由是保障人的语言能力和其他先天认知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的必要条件,一个理想社会必须提供符合人性发展的环境,使人成为自由、自主的个体。乔姆斯基的这种在语言哲学思想影响下所产生的自由观有其独特性,它把人的本质与价值看作是自由的基础和目的,把人天生的心智机能看作是自由的限度,把言论和思想自由放在核心位置,丰富了自由的内涵,同时,也为乔姆斯基语言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契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平台。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观集中地体现为心灵主义、自然主义、内在主义、个人主义和“最佳理论”,他的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的基本理论主张在本质上是超越于传统的经验主义分析哲学的。心灵主义指的是,用计算―表征论去研究人类的语言知识;自然主义是指,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与思维;内在主义强调研究人脑内部的抽象表征;而个人主义是指,所研究的大脑内部状态是个体性的而非集体性的。乔姆斯基认为,普遍语法和个别语法是存在于世界的真实物体;但他对描述二者的理论术语和论断的实在性,采取“最佳理论”研究态度。乔姆斯基语法理论的产生有其思想文化理论背景,早期受笛卡尔影响最深,同时康德哲学对乔姆斯基语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作用。乔姆斯基语法理论中的“生成能力”和“语法规则”是有同一性意义的。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生成能力是语言哲学规则的潜在形态,语言哲学规则是语言生成能力的外在显现,并可表达为语言哲学的形式系统,语言使用者关于语言哲学的规则系统的基础知识即为语言的生成能力。[6]
基于批判行为主义的语言理论,乔姆斯基提出了先天语言机制的假说,并更进一步发展出了语言模块性思想。乔姆斯基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础,提出了语言本能的假说,并明确提出语言模块是一种进化而来的适应机制[7]。达尔文认为语言的进化是一种逐渐发生的、自然选择的过程;而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语言突现进化论者认为,基因突变诱发了语言的产生及进化。对此,乔姆斯基是认同的,乔姆斯基提倡唯理论、普遍论与进化论。唯理论是其语言天赋论萌芽的土壤,普遍语法是普遍主义在语言理论中的具体体现,语言天赋论告别了古典唯理论里的“灵魂”与“上帝”,走向了同样具有不朽与万能品质的生物“基因”。乔姆斯基从语言哲学角度进行了相关论证,可以从四大方面进行具体分析:一是问题的发现和提出,二是多角度论证普遍语法的存在,三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辅假设、理想化、最佳理论、溯因推理、直觉证据等),四是内在化语言研究的意义。在使每个方面论证内容具体化、论证思路清晰化的基础上对生成理论进一步评价、批判和发展才成为可能。乔姆斯基的先天语言机制的假说为后来乔姆斯基提出“转换生成语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犹如康德的先天知性形式和“图式”哲学思想,其人文精神在于揭示人类心智和思维特征的普遍性,进而可以把人定义为“语言符号的动物”。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批判了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否定了结构主义的认识论,运用笛卡尔等人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对语言现象做出了系统完整的哲学解释。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反映了人类的心理活动,人类的语言能力包含“天赋”成分,这和马克思强调的语言是“实践性的人类思维活动的体现”的语言哲学思想有相通之处。[8]同时,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还是一个包含了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语言的内在性和自然性、语言的普遍性和个性的三个方面辩证统一思想的完整的语言哲学体系,而这一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他所提出的语言内在性。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使用形成人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在基本语言层面,语言建构人的主体性,为人类表征世界提供可解读的思维资源。[9]在功能语言层面,功能性语言标记又使主体间性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可以看作是一种形式化语法,是人类语言能力模式的哲学表述。它研究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分析人的内在语法来揭示出操任何语言的人都具有的“普遍语法”,或者说,通过探索人脑中的语言能力来解释人的生理机制,揭示人类自然语言习得的奥秘。
三、乔姆斯基语言哲学与马克
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契合
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哲学是系统化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语言哲学是研究语言学与哲学共同规律的科学,它属于交叉学科。语言和语言哲学研究是西方现代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代表了哲学范式由认识论形而上学向语言哲学的第三次语言哲学的转向。自此,语言的地位得到迅速提升,语言不再是人与人交流时所使用的透明工具,而是变为一个特殊的在者。西方语言哲学自古希腊开始,先后经历了古代本体论和近代认识论,已经进入现代语言哲学论的新时代。在此语境下,由于语言从交际工具变成人的存在方式,所以语言哲学不仅成为哲学的前沿分支学科,而且成为西方人文科学的时代标志,这也使得语言哲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出现了风生水起、方兴未艾的情况。
沿着恩格斯的经典文献《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开辟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轨道,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詹明信的《语言的牢笼》成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承前启后的宝贵思想财富。马克思强调的是语言的“实践性”;沃洛希诺夫突出的是语言的“对话性”;詹明信凸显的是语言的“辩证性”。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是在批判两种语言哲学流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两种语言哲学流派的对立提供了融合、对话的可能,为我们重新审视英美经验主义语言学和欧陆先验语言学传统提供了超越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视角。根据马克思对于语言的“实践性”的观点来看,语言使用形成人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在基本语言层面,语言建构人的主体性,为人类表征世界提供资源。在功能语言层面,功能性语言标记又使主体间性成为可能。人的主体性在语言作用下走向主体间性是一种哲学必然。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前主体性、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断凸显。[10]主体间性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共识问题。话语是人根据自身目的对语言系统进行选择的结果,是主体间性的重要表征方式。话语既是人自身目的的外显,又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手段。目的、话语与主体间性三者之间密切联系,主体间交际目的的协商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动因。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根本特色在于,它既体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一般趋势,又具有较强的西方传统哲学的特征。它主张,从感觉、直觉到概念的发展过程,就是语言从实体到功能、从直接到间接、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不断发展过程,象征着人的文化创造性的不断成长。它将语言作为人类文化创造的总体性维度,通过对语言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进程的文化哲学分析,彰显了语言在人类文化中的独特地位,揭示了人类特有的精神本质和能力。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其本质上是将语言看作客观存在,这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相吻合。马克思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通过实践了解物质之间的关系,并且用范畴和概念来理解世界。外部世界是客观现实的存在,客观存在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具有真实性。语言具有固定意义,人们只要用清晰和准确的定义是可以触及客观的。在获得语言固定意义和清晰定位的过程中,应避免使用隐喻和其他的修辞手段,这样的表述或多或少的有些生硬,这也可能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较少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11]
西方传统语言哲学强调人们的日常实践凭借感知,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感觉、道德、美学和精神意识,人们是通过想象而非理性获得意义的,经验现实主义将主观与客观有机地结合到一起。经验现实主义在认知隐喻中得以充分体现。人们是通过想象性推理而获得意义的。意义蕴于人体机能和社会经验,意义的结构源于概念之先的结构,抽象的概念源于隐喻和换喻的映射。西方当代语言哲学则更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这种观点,认为主观与客观是互动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生硬。正是在此语境下,19世纪以来,西方的语言哲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乔姆斯基借助维特根斯坦、洪堡特、笛卡尔与皮尔士等人的语言哲学思想建构起自己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理论。一条绳子不是因为其中有一条贯一的线,而是线的相互纠结和交织。乔姆斯基的这种唯理主义思想起源于柏拉图,但主要是在批判和继承笛卡儿和洪堡特的基础上形成的,他的唯理主义不仅克服了前辈思想家的二元论,而且还与无政府主义、唯意志论、经典自由主义等相联系,为其语言研究和政治研究的最终统一创造条件。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吸收与批评也使得他获得了更高的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乔姆斯基认为存在“人类共有的、先于经验而存在于个人之中的、无差别的绝对共性”的语言。[12]我们可以假定有先天的语言器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对其进行清晰的描述,我们所有的语言理论只不过是一种对相关语言现象的解释而已。究其实质而言,这和马克思所强调的语言的“实践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乔姆斯基的语言学方法体系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他看到了当时的美国经验主义语言学的缺陷,他大胆采用了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运用了结构主义和理想化、形式化的方法等,把语言学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强调语言的“实践性”。[13]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审视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的相关理论,就会发现,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及其方法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相对性,这和他的理论的开放性和相对性是统一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价值,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理论及其方法论,对于当代中国的语言哲学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当然,其建构是以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思想为基本前提。
四、乔姆斯基语言哲学对中国语言
哲学建构的当代启示
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前主体性、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断凸显。主体间性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共识问题。话语是人根据自身目的对语言系统进行选择的结果,是主体间性的重要表征方式。话语既是人自身目的的外显,又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手段。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强调目的、话语与主体间性三者之间密切联系,主体间交际目的的协商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动因。乔姆斯基语言哲学认为语言的主体性、模糊性以及建构性等特征使得语言不可能完全精确地表述客观事物;人类作为认识主体,对知识和意义的建构是在诸多动态的语境中发生的。
中国语言哲学需要一种建立在自然语言基础上的元语言。中国语言哲学体系中的元语言是人类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在这一点上,我国语言学若要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派,不妨学习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研究路径:由世界进、从语言出,着力语言学思想的创新。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哲学命题的解构分析,更应该展开元语言的建构,即通过转换语言结构分析程序建构出反映认识范畴的表达式。比如概念分类和整体切分作为不同的认识范畴,通过日常语言学派的词语用法分析不容易区分开,通过转换分析建构出表达式,可以有效地得到区分,相关的外延扩大和限制问题也能得到解释。乔姆斯基语言哲学强调各类语境在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过程中,并不孤立存在,在现实的语言学习中,建构合理的语境,形成有效的互动协同,实现高质量的语言输入,有利于提高语言的学习效率。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也不应该忽略此点。同时,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还应强调本体论语言哲学,这是由于其独特之处在于,它除了需要研究语言的在和是以外,由于在者/是者不确定,还需要科学论证语言是在者/是者。通过追问语言本质、反思语言哲学以及界定语言哲学三个环节,初步呈现出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之路。中国语言哲学建构既要预先关注哲学中的认识范畴,也需要掌握语言结构分析程序。中国语言哲学和语言学应该有更深层次的结合。
[参考文献]
[1]范连义.“语言共性”与“家族相似性”――维特根斯坦和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思想比较研究之一[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1,(1).
[2]JA Fodor, JJ Katz, WVO Quine, N Chomsky.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1964,pp.158-163.
[3]范连义.语法的内在与外在――维特根斯坦和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思想对比研究之三[J].外语学刊,2013,(2).
[4]郭庆民.新思想产生的语言哲学基础――乔姆斯基语言哲学与批评话语理论比较述评[J].教学与研究,2011,(5).
[5]N. Chomsky. Language and nature[J].Mind, 1995,pp.41-44.
[6]刘利民.由世界进 从语言出――布龙菲尔德、蒯因、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之争及其对中国语言学学派建设的启示[J].外语学刊,2013,(1).
[7]JR Searle.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J].1969,pp.101-102.
[8]谢都全,郭应可.洪堡特与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思想比较研究[J].求索,2011,(9).
[9]王莉.乔姆斯基语言哲学中的辩证统一思想[J].求索,2010,(9).
[10]N. Chomsky. Language and problems of knowledge: The Managua lectures .1988,pp.95-97.
[11]易立新.语言问题的哲学探索――评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思想[J].外语学刊,2010,(4).
[12]N. Chomsky. Three factors in language design[J].Linguistic inquiry, 2005,pp.34-39.
[13]李曙光.理论的对话――巴赫金与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思想之间的张力[J].俄罗斯文艺,2011,(3).
The Characteristic of Chomsky's Language Philosophy and Its Enlightenment
LIU Xue-l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30, Gansu, China)
语言哲学观论文第5篇
一、《逻辑哲学论》中的哲学转向
1.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
古希腊哲学以本体论问题为核心,致力于探究世界的本原。“一切形而上学(包括它的反对者实证主义)都说着柏拉图的语言。”[1]61《逻辑哲学论》的命题1和2也论述着世界的构成,反映了世界的逻辑构造的逻辑原子主义思想。但传统的世界观认为世界就是物的集合,物和原子均可分,且按照自然科学的观点可以无限分下去,维特根斯坦却将组成世界的元素限定在了“对象”上,相应的事态就是逻辑原子,且认为“对象”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在事态中对象就像链条的环节那样互相勾连(2•03)”。命题1和2映射的本体论思想和古希腊时期自然哲学家们讨论的本体论已有很大差异,超越了古希腊时期对世界、对自然朴素的态度,超越了古希腊时期对本体论问题的两种解释方式———以某种具体的物质作本原来解释世界和以数作本原来解释世界。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哲学就包含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等三种知识,前两者属于本体论的研究范围,而逻辑学则属于认识论范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别从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中分化,加之近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和实证主义的影响,近代西方哲学排斥对形而上学的研究,这就导致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心理学和逻辑分析的方法较多被采用,分析和归纳成为近代认识论的关键词。《逻辑哲学论》的命题3和命题4提出的图像论恰好反映了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这两个命题提出了关于思想和命题的图像论,阐述了关于事实、逻辑图像和思想的关系。思想被看做是事实的镜子,因为事实的逻辑结构就反映在思想中。维特根斯坦指出事实存在于逻辑空间中,而不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每个事物都像是在一个可能事态的空间里。我可以设想这个空间是空的,但是我不能设想没有这空间的事物(2•013)。”其中的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的关系怎样?逻辑上的可能世界如何才能达到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如何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寻求知识的确定性?必定有一种连结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共同的东西。维特根斯坦认为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思想,而思想又是在逻辑空间中的活动,所以现实世界中的图像是由逻辑形式为我们所认识的。我们都是根据逻辑在思想,“我们不能思想非逻辑的东西,否则我们就必须非逻辑地思想(3•03)”。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阐释了思想以逻辑为工具对事实的把握,它用图像来联系事实领域和命题领域。“图像就成了区分真正的命题与似是而非的命题的标准,它为命题与非命题划定了界限。”[2]438
2.从认识论向语言学的转向
西方哲学经历了古代强调对客体世界本原进行探究的本体论时代、近代强调对人类认识的本质、结构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追寻的认识论时代,以及当下强调对作为认识工具和思想表达形式的语言进行探究的语言学时代。“当今各种哲学研究,都涉及一个共同的研究领域,这个领域就是语言。”《逻辑哲学论》命题5和6强调了语言和命题是思想表达的手段。维特根斯坦将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的问题,“全部哲学都是一种语言批判(4•0031)”。此论述实际隐含了西方哲学由认识论向语言学的转向。在自然科学领域,由于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物理学由宏观领域转向微观领域,导致物理学传统范式“解题能力”的弱化。认识论困境部分导致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我们理解和表达思想的方式只能是语言,我们在谈论思想时其实是在谈论语言,所以语言必须符合逻辑。“在语言中不能表现任何‘违反逻辑’的东西,就像在几何学中不能用坐标来表现违反空间规律的图形,或者给出一个并不存在的点的坐标一样(3•032)”,否则就会出现歧义和理解混乱。在罗素的导言中就明确提出:“传统的哲学和传统的解决是怎样由于符号系统原则的无知和对语言的误用而产生出来的。”[3]3维特根斯坦把传统哲学的错误看做是错误地使用语言的结果,因此《逻辑哲学论》就是要通过解释日常语言的逻辑缺陷表明传统哲学的错误根源。所以解决哲学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理清语言自身的逻辑与日常应用。只要语言符合逻辑就可以通过它找到知识的确定性。“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5•6)。”要在哲学研究方法上进行逻辑主义的思维,必须将传统研究方法从“主观”转向“客观”,即从主观的思维逻辑转向客观的语言逻辑。
二、实践解释学的方法论意蕴
国内学者俞吾金强调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理论穿透力,认为马克思在解释学领域中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一革命的“主旨是确立实践在人的全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的核心作用”[4]5。实践解释学不同于解释学哲学、哲学解释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解释学等范畴,实践解释学以实践取向的唯物主义为背景,建立了世界和人的“意义性”关联和“解释学关联”。它是实践的、历史的、批判的、总体性的解释学方法,“使语言、文本、结构、观念通过实践向生活、历史、人、现实开放,形成语言与生活之间的解释学循环、文本与历史之间的解释学循环、结构与人之间的解释学循环以及观念与现实之间的解释学循环”[5]47-50。哲学是一项澄清思想的实践,而语言又是表达思想的手段,可以说,哲学是一项澄清语言并使其有意义的实践。既然如此,理解和解释在此过程中就不可或缺。而要避免误解,解释学在澄清思想上又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如法国解释学家保罗•利科尔给解释学下的定义,“解释学是关于与文字相关联的理解过程的理论,其主导思想是作为文本的话语的实现问题”。施莱尔马赫也认为,“哪里有误解,哪里就有解释学”[6]41-45。在他看来,“误解是普遍的,而解释是避免误解的艺术,理解需要解释规则系统的帮助,排除误解,达到正确的理解”[7]113。实践解释学把对象和现实看做是主体实践的结果,对象和现实的“属人意义”必须通过实践活动来得到理解。由于语言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所以这种辨证唯物主义观点为我们理解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使得语言批判具有了实践解释学意味———我们可以对“可说的”进行基于实践的解释,对“不可说的”进行基于实践的理解。解释和理解的区分导源于J.德罗伊森的《历史概论》(1858)和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1883),它在抵制自然科学方法的背景下提出,凸显了人文科学的独特视域,对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解释学具有启发意义,且对我们分析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三、实践解释学视域中的《逻辑哲学论》
维特根斯坦一直认为世界以两种形式存在,即“可以说的”与“不可以说的”。所谓“可以说的”就是能够用逻辑语言言说的东西,而“不可说的”就是无法用逻辑语言表达的东西。《逻辑哲学论》的前六个命题特别是命题5和命题6主要分析了“可说的东西”,而作为一个没有子命题的独立命题,命题7则意犹未尽却清楚明白地表达了对“不可说的东西”的态度,与前述其他命题中体现出的对“可以说的”事物的态度———用逻辑语言说清楚———形成了鲜明对比。根据我国学者俞吾金和李金辉的观点,我们认为哲学不应该回避“不可说的”,而应从实践解释学视角回应或处理“不可说的”问题。
1.“可说的”———基于实践的解释
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的使命不是提出命题,而是要澄清命题,即从逻辑上解释清楚思想。但语言并非是完全符合逻辑的,而且即便是符合逻辑的语言也并非能完成语言的使命———能够应用于日常表述,如科学世界的语言就无法应用于生活世界。传统哲学弊病的根源在于它总是试图去创造一些不可说的、无法用逻辑语言解释的命题。这样的形而上的命题都是无意义的命题。与形而上的命题相对,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中正确的方法是:除了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与哲学无关的某种东西之外,就不再说什么。而且,一旦有不想说的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时,立刻就向他指明,他没有给他的命题中的某些记号以称谓(6•53)。”因此,“哲学的目的是从逻辑上澄清理解,哲学不是一门学说,而是一项活动。哲学著作从本质上来看是由一定解释构成的,哲学成果不是一些哲学命题,而是哲学的澄清(4•1112)”。我们认为,哲学澄清的本质即基于实践的解释。解释(Explain)由表示“外面”和“以前”的前缀Ex-和表示“简单易懂”的词根plain组成,它意味着“从外面对世界进行简单易懂的研究”。此种意义上的“解释”正好对应着科学与哲学分野后的科学知识,亦即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这种解释性的澄清也应该以逻辑分析或语言分析为基础。问题在于,逻辑分析或语言分析与实践紧密相连。实践解释学中的实践概念是需要解释的、受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并随着这种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概念。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所提出的“语言游戏说”明确指出,语言和词语都是工具,其意义取决于其用法。“语言的用法十分繁多,每个个别的语言表达(陈述、问题、命令等)都嵌在比较广阔的语言和超语言行为的环境之中,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2]440这一思想与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有一定重合之处。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有多重含义,我国学者李金辉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文本梳理,认为“实践”经历了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哲学上的和总体性的概念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实践的演变过程。[8]34很明显,包括语法、语义和语用等在内的语言是实践本身或实践的产物。因此,我们认为对“可说的东西”进行批判,就是对作为实践的语言进行解释。
2.“不可说的”———基于实践的理解
维特根斯坦认为,“真命题的总体就是全新自然科学(或自然科学的总体)(4•11)”,而“哲学不是自然科学之一(4•111)”。所以,哲学所提的命题就不是真命题,但哲学又并非无用,它“为自然科学划定可以在其中争论的范围(4•113)”。哲学应当为能思考的东西划定界限,从而也为不能思考的东西划定界限(4•113),而且,“没有哲学,思想就会模糊不清(4•112)”。由此可见,哲学命题虽然不是自然科学命题中的真命题,但仍然有实践价值。因此,我们不能轻率地像维特根斯坦那样将哲学命题划归为“不可说的”而对其保持沉默,而应该对其进行实践解释学分析,即基于实践的理解。伽达默尔将解释学当做一种方法和注释文本的技术,海德格尔则将解释学当做“哲学”,注重对存在本身———定在的本体论诠释。将解释学由“方法、技艺”看做是“哲学”,导致了认识论的基础与本体论的基础的对立。然而在阐明某些概念这一哲学任务中,认识和本体并不是对立的,而应是统一的。正如利科尔所说:“解释学不是对人文科学的思考,而是对人文科学据此建立的本体论基础的说明。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关键的一句话是:因此,被看作是解释学的内部包含着在引申意义上被称为是解释学的东西的根基:人文科学方法论。”[6]54按照狄尔泰的观点,“我们把从通过感官接收的符号中识别出某种内在内容的过程称为理解”。而理解(Interpreta-tion)英语前缀Inter即有“内在”和“相互”之意。在解释学的意义上,所谓“理解”就是人的一种通过反身性达到内在性的把握的过程。“理解”意义上的展现,不是那种人不在场的自在过程,而是人的现实活动开启并参与生成的过程。[9]1-3此种“理解”方法是人文科学方法论,可以作为哲学命题分析的基础。作为人文科学方法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将“不可说的东西”说清楚,这依赖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的行动和实践。维特根斯坦认为,“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4)”、“关于哲学问题所写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4•003)”。要揭示被掩盖意义的问题,就需要主客体双向度理解。而这种特殊实践就是解释主体和解释客体间的双向互动行为,而不是单向度的注释。历史解释学认为,生存实践属于人类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因此,实践不是苍白的行动,而是包含着历史、传统和文化等背景要素。施莱尔马赫所要避免的“误解的理解”就是单向度的无背景参与的理解。
如果哲学的解释活动是单向度的,那么它也就只能如维特根斯坦的命题7“对凡是不可以说的就必须保持沉默”了。因为单向度的理解“就只能是对我们熟悉的、已知的和我们一样充满‘精神’的生命世界的理解,对于我们不熟悉、未知的世界理解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认识。这种认识只能通过实践的超越性来进行。实践的超越性克服了主体和对象之间的解释学间距”[7]115。对这些我们不熟悉、未知的世界只能进行外在解释,而不是内在理解。因此,实践是处在一定文化背景、一定解释学前见之下的活动。要突破单向度理解的视域限制,跨越利科尔所称的“解释学间距”,就要搭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桥梁,使主体客体化和使客体主体化。
语言哲学观论文第6篇
从远古时代起,哲学问题就与语言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以来,语言就成为哲学的主题。有关语言哲学的探讨,反映了哲学思想的存在须臾不能脱离语言,因为思想的对象与思想过程本身,都必须依靠语言才能转变成他人思想所能把握的东西。[1]1维特根斯坦认为一切哲学都是“对语言的批判”。[2]可见,分析语言和语言现象是语言学、语言哲学的共同特点和任务,“两者不仅不相互疏离,而且相互依存,相互促进”。[3]24哲学进入语言领域,把语言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或试图通过语言分析来解决哲学问题,成为当今学术研究领域的新亮点,为语用学研究和哲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维索尔伦的顺应论从共时的角度展现了语用学的跨学科性质,说明了当今的语言学研究在向其他人文学科输出思想的同时,也从其他学科(特别是哲学)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本文结合顺应理论,对语言哲学意义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推动语用学和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一、语言顺应理论
语言顺应理论是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维索尔伦(vers-chueren)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认识论思想,结合人类语言交际的实际情况于1999年在《语用学新解》一书中提出来的。语言顺应理论是一种关于人类语言交际行为和认知的理论。它以语言的选择与顺应为契机,描述人类使用语言的各种现象,阐释人类语言交际的心理机制及其过程以及社会、文化、认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出语言运用的实质。顺应论认为,语言的使用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过程是动态的,是以语言的三种特性(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为基础的。变异性(variability)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negotiability)指“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的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做出的,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顺应性(adaptability)指“能够让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事项中作灵活的变通,从而满际的需要”[4]59-61。语言的这三种特性互为关联,以顺应性为主要特征,从四个方面去阐述语言的使用:语境关系顺应、结构对象顺应、动态顺应以及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4]65-66顺应论对语境的划分充分考虑了社会、文化因素,将语境分为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前者指语言在使用过程中根据语境因素而选择的各种手段,后者包括语言使用者、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简言之,语言的选择与顺应,从本质上讲就是“语言是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系列适应现象之一”[4]266。顺应理论引发了人们对语言本质问题的重新思考,加深了人们对语言本质属性的理解和认识,启发我们在选择和使用语言的同时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进行哲学思考。[4]
二、顺应理论与语言哲学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带来了语言哲学的迅猛发展,许多哲学家都把研究语言置于解决哲学问题的中心地位,语言成为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海德格尔把语言与本体论相联系,并把语言当成人的本质属性。他说“语言是人的世界,是存在的住所”[5]157。维特根斯坦认为“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方式”[6]13。迦达默尔也赋予语言本体论地位,主张人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只有进入了语言的世界才是人的世界,只有进入语言的生活才是人类的生活,人、语言和世界是密不可分的。他认为“语言是一种在其使用中自由而可变的人的能力。对于人来说,语言本身是可变的,因为它对于同一件事为人准备了各种表述的可能性”[7]577。因此,维索尔伦将他的语言顺应理论界定为“一种与人类诸种行为中的语言现象的使用相关的,且从认知的、社会的、文化的总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4]7,意蕴深刻。首先,作为一种语用学理论,语言顺应论所研究的语言使用现象和人类的诸种活动形式不可分离;语言表意功能的发挥是在被嵌入或锚定于这些活动形式中才得以产生、发展和完成的。这种观点至少反映了人类学、哲学和符号学对语言本质的看法。[8]130可以说,语言顺应理论在其理论基础层面,从一开始就带有浓浓的生物学、符号学、人类学和(语言)哲学意蕴。这是它区别于其他语用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言作为一种活动形式是被嵌入到人类的合作性活动中才发挥其语用功能的。所以要研究语言的意义和功能,就必须考察这些作为语言活动形式的人类合作性活动。人类学家对语言问题的思考与哲学家对语言使用过程的观察和研究是相符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在思考语言(意义)问题时提出的语言游戏说就包括“语言和语言被织入其中的活动”两个组成部分。而语言使用作为语言游戏活动总体中的一部分是被织入其中而发挥其功能的。马林诺夫斯基和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意义的语用观在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在莫里斯的体系中,语用学的研究对象是符号与符号解释者(后成为使用者)之间的关系。[8]131其次,维索尔伦认为语言顺应论是“从认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总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4]7。“综观”作为观察语言使用的一种理论视角反映了维索尔伦对语用学本质的独特理解,但其构成要素则有着深厚的符号学、哲学渊源。莫里斯在将语用学定义为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进一步认为语用学研究符号表意过程中涉及的生命特性,即在符号发挥功能的过程中出现的所有心理、生物和社会现象。在哲学层面上,维特根斯坦在解释语词意义的生成过程时提出语言游戏来说明语词意义生成过程的动态性质,从而得出“意义即用法”的观点,并提出“生活形式”来说明意义生成的本体。[8]132总之,维索尔伦认为,语言使用和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生活密不可分:二者之间既相互影响,也相互顺应。语言之所以如此乃是其顺应人类生活的结果,而人类生活之所以如此也来自其对语言使用过程的顺应。这正是语言顺应论的基本要义。
三、顺应论蕴含的哲学思想
语言顺应论突破了言语适应理论长期遗忘语言、谈语言作用这一瓶颈问题,使语言问题回归语言本身,革新了言语适应理论的研究,展示了语用学研究的新理路。具体而言,维索尔伦顺应理论所蕴含的语言哲学思想大致如下:#p#分页标题#e#
1.进化认识论思想。维索尔伦的《语用学新解》一书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是怎样作出贡献的?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4]55?人类生命和人类社会是个逐步进化的过程。要探究语言在这一过程所起的作用,必须探究语言是怎样以及为何被使用的,与人类社会和生命的进化有何相似之处。根据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必然经历自然选择和适应两个过程。选择是手段,适应是目的和结果[9]54。“顺应”这个概念最早见于生物进化论。在生物学中,顺应指生物体调整自己以适合环境的过程,是生物体为了生存而对自然选择范式作出的反应。在进化认识论中,这种观点被扩展至人类的行为、心理和社会-文化诸方面,用于解释人类的学习、语言的使用和发展以及科学知识的增长。进化认识论认为,人类的认识活动表现为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的问题求解,其目的是增长科学知识,而人类的行为和社会-文化正是这种顺应的结果之一。[8]129维索尔伦在考察语言使用中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即选择与适应的思想。认为语言使用中选择时的趋优(利)心理与自然选择的存优去劣是极其相似的。既然在语言使用中选择普遍存在,顺应也自然具有普遍性。语言顺应的本质就是“语言是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系列适应现象之一”[4]266。
2.动态的意义观思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哲学史上发生的“语言转向”使人们关注的焦点从认识的本质、起源等问题转到了探究语言的意义问题上。意义问题成为转向之后语言哲学研究的基础和核心。[1]38语言既是一种交际工具与符号,更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一个特殊在者或是者。同时语言又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伴随人脑的出现而出现的。确切地说,语言,不论是作为对象工具还是在者本体,也不论其自然属性还是社会属性,都是思维物质器官大脑的产物,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语言的产生并决定着语言的意义。语言、思维与世界相互关联,共存于意义产生的动态演变体系之中。维特根斯坦在他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提出了“语言游戏说”和“意义用法说”,把意义归结为语言在实际生活中的使用。语言哲学的任务在于研究日常语言的用法,语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6]他的这一观点不仅奠定了后来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分析语言意义的基础,而且为语用学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他的影响下,奥斯汀、塞尔等人逐步从一种全新的角度研究意义问题,提出言语行为理论,即将语言表达视为行为方式。后来利奇[10]的礼貌原则强调从社会的角度对言语运用进行研究;而斯珀伯与威尔逊[11]提出的关联理论则强调从认知的角度研究言语运用。这些各有侧重的研究都不能充分有效地解释言语运用的全貌。维索尔伦希望改变这种语用学研究中的传统、走出困境,因此他接受了达尔文选择与适应的进化认识论思想,从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中直接借用了“适应”观点,并对社会语言学中的言语适应理论进行借鉴和革新,于1999年在《语用学新解》中提出了语用综观顺应论。维索尔伦的意义观从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日常语言研究中功用论的思想,用商讨性和变异性来概括语言意义的特点。同时维氏也继承了功能主义的语言观,动态地考察语言的动态功能,这与他的研究目标“语言与人类生命的其他特征的功能相关性”是一致的。[12]52-53顺应理论体现了语言使用者在言语交际过程中顺应交际条件而对语言的内容和形式不断作出恰当的选择。所以说语言的使用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意义就是语言使用者在言语交际过程中通过不断选择、互动、协商、顺应而建构出来的。因此,维索尔伦的意义观关注的就是语言使用是否得当的问题,这正是它与以往意义观的根本区别。维索尔伦认为,语言不是一个封闭的、单一的静止系统,而是一个与认知世界、人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融合在一起的、呈现出开放性和多元性的动态系统。意义就是在动态的选择中、在多样的语境中和交际者不同的心理认知参与构成的交互网络中生成和得到解释,从而达到人与人之间的顺应和人与客观世界的顺应。维氏的顺应论完整地体现了语言即选择的观点,探求语言意义就是主动选择和社会建构的行为。
3.动态的语境观思想。任何言语交际都离不开一定的语境。交际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交际过程中,语境也随之而变。交际过程也是语境的构建过程。[13]21-22莫里斯(Morris)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语用学是研究语言现象和语言使用者关系的学问。[14]52然而,纵观以往学者对语境的研究,他们都未能明确指出交际者在语言使用中的重要作用。维索尔伦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次明确提出一个以交际双方为中心的语境关系顺应框架,指出语言使用者在语境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交际双方作为言语交流主体平等的关系,认为语境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概念[14]52;同时从顺应性的角度全面探讨了语境的本质属性:动态生成性。即语境不是静态的,而是产生于交际双方使用语言的过程中,由不断被激活的因素和一些客观存在的事物相互作用而动态生成,并随交际过程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维氏指出:语言顺应的本质就是“语言是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系列适应现象之一”[4]266。语言顺应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或多维的,顺应既可以是语言顺应环境,也可是环境顺应语言,或者两者同时顺应,还可是交际主体的彼此顺应。[15]85可见语言与语境相互顺应的过程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所以,语言顺应的社会维度、文化维度和认知维度都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都是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维氏把动态顺应作为其语用综观顺应论的核心。
语言哲学观论文第7篇
关键词: 语言学语言哲学关系
一、引言
从哲学产生之初,语言问题就包含在哲学思想之中,只是人们一直将语言作为再现事物的本质、表达思想的工具。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家关注的是万物的本体问题;近代以后,认识活动的主体及其所使用的认识方法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而在语言学界,现今一般把语言学分为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两部分,并且认为理论语言学应当是应用语言学的方法论。对语言进行实证性研究是语言学的主要部分,同时它需要理论语言学作指导、作方法论,但是理论语言学又应当以什么作为指导和方法论呢?答案应是:哲学。
理论语言学之所以和哲学密不可分,是因为只有哲学是涉及面最广、概括程度最高、涉及的问题最为复杂和抽象的科学,而且哲学研究的突出特点是穷根究底,并且打破任何学科界限,因此理论语言学必须和哲学研究紧密结合,并且在正确的哲学学说指导下,同时吸收和采纳实证语言学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才能正确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使理论语言学研究不断获得突破和进展。
二、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关系
哲学是语言学的基石。历史上每次语言学的重大变革都是以哲学的突破性进展为先导的。而语言哲学最基本的问题便是语言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认为应使哲学成为一门严密科学,凭借“直接地认识”来描述现象,把“现象”、“本质”、“描述”等同起来,使哲学最大限度地获得表述的明晰性,从而突出了语言的重要性。在胡塞尔之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等学者对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在海德格尔看来,从柏拉图以来的传统的形而上学颠倒了语言和人的关系,语言从一种“它在”变成了属我(人)之物,从而晦蔽了存在:“正是语言最先造成了威胁和模糊存在的明显状况,也就是造成了失去存在的可能性。”要真正理解语言的本质,就必须将长期被颠倒的语言和人的关系再颠倒过来。所谓语言的“它在”是指语言只是作为“存在之家”而在,但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又注定了召唤人的栖居。人必居于“在”之中,即必居于语言之中。于是,“语言控制着人生存的最高可能性”。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具有“此性”和“彼性”之分,语言的此性使人们堕入跟随“公众意见”的现世沉沦。而语言的彼性则是作为“无物的声音而默默到来的,它将人唤过喧嚣在耳的公众意见(此)而面临虚无(彼)。”人通过超越“此”而走向“彼”即是走向这种去蔽以后回归始初状态的本真语言――诗性语言。诗性语言昭示出被世人遗忘了的人与自然的非世界性关系,使人获得了在大地上生存的本质――“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因此,海德格尔所提出的诗之思在根本上是一场关于语言、存在、真理的对话,如他所说:“思与诗的对话是为了唤出语言的本性,以便必死之人得以重新学会生存在语言中。”在海德格尔这里,诗与思的对话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生存的决断,语言问题被提到了此在的本体论高度。
海德格尔的弟子伽达默尔创立了现代哲学解释学。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他批判了各种语言工具论。他通过对词源学和哲学史的考察,指出西方哲学的中心概念logos(逻各斯)在其本来含义上,是作为语词与对象的统一体,而到柏拉图时代则分裂为对立的二元。柏拉图关于语言的理论就建立在客体或理念对语言的先在性前提上,从此西方哲学开始了摆脱语言控制又反过来控制语言的漫长过程,“而处于这个方向尽头的是近代关于语言的工具理论和理性的符号系统的理想,挤在图象和符号之间的语言存在只能被认作纯符号存在”。他继承海德格尔的思路,把“语言”问题和“存在”问题结合起来,认为语言就是我们“存在于世”起作用的基本方式,也是世界构成的无所不包的形式。而“诗歌的、艺术的语言”才具有唯一美的显现的直接性和完满性。借助于这种美的显现的直接性和完满性,人们就可以实现对本真的回忆和重新认识。哲学语言通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转向了另一个天地――艺术的、诗的语言。用伽达默尔的话说,这是“原始性语言力量在思想领域中的突发”,“‘语言’因此以全部直观力对其生活世界的持久性根基来说成为至关紧要的;……势所必然,语言本身成为它在哲学上的自我把握的对象”。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哲学家们试图以语言为中心建立起一个反二元论的意义整体。在他们看来,语言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形式或纯工具,而成为唯一的结构化的现实,关于世界的语言经验上升为绝对的东西。原先在认知过程里被当作一种透明介质的语言,接受了哲学家们从各个角度的聚焦透视。
从总体上说,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粉碎了传统形而上学的镜式语言观,将语言作为一个中心点进行了全方位的观照,语言不再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静止的镜子,而是承载着意义和真理的存在。这种转向为哲学确立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导致了思维领域内的根本性革命。
(二)结构主义和语言学
“在当代各种哲学思潮中,其语言学基础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结构主义了”。语言学家布洛克曼强调:“要是离开了语言学……罗兰・巴尔特的文学批评都是不可想象的。对于哲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中结构主义所作的认识论的研究来说,现代语言学所起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种数学的作用。”
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及其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加上后来分化、发展而成的“转换――生成语法”是结构主义产生的直接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主要包括:(1)语言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词项所组成的符号系统,词项的意义依赖于词项之间的关系;(2)语言与言语不同,前者是社会的现象,后者则是个人的现象,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应是语言,而不是言语;(3)语言现象是一定时间互相并列、互相依存、互相制约而自成一体的符号系统,因此要对语言进行“共时”研究,而非“历时”研究。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分为三个支派:以特鲁别茨柯依(H.C.Tpyoellkoia)和雅各布逊(R.Jakob-son)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又称布拉格音位学学派;另一支派是以叶尔姆斯列夫(L.Hjelmslev)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亦称语符学派;第三个支派是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俗称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其代表是布龙菲尔德(L.Bloomfield)和霍凯特(C.F.Hockett)。他们共同的观点是:“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符号系统,强调共时语言的重要性,强调分析、研究语言的内在结构。”
20世纪50年代,从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中分化、发展出一个新的语言学派,即“转换――生成语法”学派,其创始人是乔姆斯基(N.Chomsky)。他的语言学理论的中心是关于“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理论。他认为,人类每一种语言系统都具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这两个层次。表层结构是人们可以“说出、写出、听到、看到的”,而深层结构是“存在于说话者、写作者、听者或读者的心里的”。深层结构是表层结构的基础,深层结构经过转换规则生成表层结构。在此基础上,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能力而不是语言运用。只有正确地描写出说本族语言的人的内在语言能力,这种语法的描写才是充分的”。显而易见,尽管乔姆斯基的“转换一生成语法”在很多方面对传统语言学理论有了革命性的发展,但就其理论的本质而言,仍能清晰地看出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理论的痕迹。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是索绪尔,而(普通意义上的)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则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列维――斯特劳斯全面接受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观点,并把结构主义的方法运用于自己的人类学研究。他指出:“语言学并非像其他学科那样只是一个社会学科而已,而是大大推进了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学科。语言学也许是唯一可以真正称为科学的社会科学学科,也是唯一获得了经验方法规则,同时获得了对其所分析的材料之本质进行理解的规则的学科。”
1957年乔姆斯基的名著《句法结构》一书出版,列维――斯特劳斯在深入研读了之后认为乔姆斯基在语言学中所作出的先验论的哲学观点具有普遍的意义,因而他很快就将它运用于人类学研究。
结构主义的其他代表人物还有:历史学和科学史方面的福科(M.Foucault),文艺理论方面的巴尔特(R.Barthes),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的阿尔图塞(L.Althusser)。
福科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他一生致力于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模式去挖掘和分析知识的统一结构,他把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用在历史研究上,建立了“知识考古学”。在他的“爆炸性”著作《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hoses)中,福科“试图通过回到语言的基础来重新建构普遍的历史”。在该书中,福科阐述了从文艺复兴到现代西方思想的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文艺复兴”时期(16世纪)。福科认为,这个时期西方文化的构成原则是“相似关系”。无论是语言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是可见与不可见事物的知识,都是由“相似关系”原则来组织和控制的。其次是“古典时期”(17,18世纪)。这个时期的知识构成是以秩序概念为基础的,而秩序又是以同一和差别的原则为前提的。最后是“现代时期”(19世纪及以后)。现代时期的知识构成原则是“根源”,这个时期的知识是追求深层根源和历史性的知识。在书的结尾部分,福科总结性地阐述道:“人类社会的文化及其历史,不论其表象如何杂乱无章,它们都受到内在的深层结构的制约。”
(三)体验哲学和语言学
在体验哲学之前,历史上曾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曾在浪漫主义诗学中盛行的主观主义,认为诗人将心中的情感投射给世界,世间万物就会因此产生诗一般的语言,即诗歌有效的起因是诗人内心的情感激动和寻求表现的欲望。另一种是以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Descartes)和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Kant)为代表的客观主义,认为世界是由相互独立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两部分构成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弗雷格(G.Frege)的客观主义语义论,即语言符号的客观意义指称某一具体事物,主观思维、想象和观念与之无关;概念是符号与事物之间的自然联系,不受人类认知方式的干预。
近年来,随着范畴化理论与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一种既不同于主观主义、又有异于客观主义的新的语言哲学诞生了,即非客观主义(non-objectivity),又称为经验现实主义(experiential realism,experientialism)或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经验现实主义语言观认为,语言不是独立于客观世界之外的符号,而是人类认知活动影响下概念结构的产物。经验是其产生的基础。经验现实主义与属于唯心主义范畴的经验主义存在本质区别。前者的经验又称为体验(embodiment),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由人的身体构造及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基本感觉――运动经验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意义的范畴结构和意象图式共同组成的人类普遍经验的总和;二是人类利用这些普遍经验来认识事物的方式,即理念化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ICMs)――语言就是该模式运动的产物。
体验哲学的思想萌芽早在Lakoff&Johnson(1980,简称L&J)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中已经初见端倪,后来的Lakoff(1987)《女人、火和危险事物》(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和L&J(1999)《体验哲学――基于身体的心智及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中又对其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详细阐述。L&J指出了传统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哲学的种种不足,因此有拒绝传统绝对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第三种选择,即体验哲学(experientialism)。
体验哲学的体验性思想来自John Dewey和Maurice Merlean-Ponty,它是建立在对Chomsky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和人类大脑就是一个像电脑这样的计算系统的反思的基础上的。体验哲学认为意义并非像前人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以索绪尔为首的结构主义者所认同的语言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像弗雷格和罗素等人的观点所言,仅仅是指符号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当然更不会只是一个简单的计算系统的功能的体现,L&J认为“意义与我们现实世界有意义的认知活动,以及通过身体体验及想象结构所获得意义的过程有着紧密的关系”。人类的语言认知能力并非像生成语法研究者所认同的那样,是一个独立的模块,人类的语言认知能力和其它认知能力是交织在一起的。语言的意义来自由我们的身体和大脑结构所带来的概念化过程。自然语言的词汇、形态和句法并非是自治的系统,他们之间形成一种相互表征结构的连续体。
他们认为认知无意识也常常是基本隐喻产生的基础,这些隐喻使我们数不清的以身体为中心的体验得以在语言层面上实现。隐喻也不是任意的识解过程,他们受我们的身体、大脑和我们日常相互作用的限制。但隐喻并不是建构,他们是概念的。初级隐喻交合在一起形成复杂的隐喻,渐渐地被大多数人接受。他们受文化的影响。他们组成了我们概念结构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对我们有意识的思考和感觉有很大的影响。语言隐喻不过是我们大脑中深层认知隐喻的体现。
总之,体验哲学在信念系统的产生及其与客观世界的联系方面的观点,主要体现在L&J所提出的三原则上,即“心智内在地说是体验的;思维大部分是无意识的;抽象概念主要是隐喻的”。体验哲学认为以乔姆斯基为首的早期认知科学假设了严格的二元论的存在,这种二元论下思想脱离身体,以他们的形式化特点来刻化。他们抛弃了乔姆斯基语言学中的形式第一位,意义是派生的主张,因为他们觉得这似乎不能很到位地解释体验哲学的基础――隐喻、格式塔(gestalt)现象、家族相似性和原形范畴理论等这些有心理现实性的东西。体验哲学认为我们的概念结构和认识图式具有完型特性(gestaltproperties),他们反对传统的二值范畴观,认为体验、家族相似论、原形范畴观和隐喻才是人类认知的真实途径。而认知语言学则极大地丰富了语言意义的研究,为语言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因而,体验哲学作为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被提出,它的认识论就很值得我们去关注、研究与利用。
三、结语
迄今的语言哲学落脚在哲学上并以哲学为目的,而理论语言学落脚在语言学上,同时以语言学为目的,但是两者研究的对象是相同的,都是人类语言。因此两者必须打通,哲学研究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实证语言科学研究是自下而上进行的,虽然这两种研究相互不能替代,但应当是互补的关系。因而,两者可以、也应当在某一个平台上汇合,找到他们的共通之处。
综上所述,理论语言学研究需要正确的哲学来指导,而实证性语言科学研究需要正确的理论语言学来指导。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先生明确指出:“语言学和哲学是最亲密的朋友,二者最应相互观照、相互渗透。”期望更多的研究者能够利用语言学和哲学的精华,在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交互关系中开辟新的认识途径,从而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更大的创新成果。
参考文献:
[1]F.de 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2]Lakoff,G&Johnson,M.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New York:Basic Books,1999:3
[3]Lakoff,G.&M.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1980.
[4]Lakoff,G.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5]陈启伟.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6]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J].哲学译丛,1992,(5):8-9.
[7]伽达默尔.摧毁与解构[J].哲学译丛,1991,(5):9-11.
[8]林玉山.现代语言学的历史与现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语言哲学观论文第8篇
关键词:哲学;语言哲学;人工语言;自然语言;语用学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8-0124-05
语言哲学之于语言学的母胎关系早在1991年就有学者[1]进行过论述,然而,真正实质上就语用学的哲学基础问题进行详细阐述的是俞东明的《语用学的哲学基础说略》一文,它对语用学的哲学背景和语用学的两大流派,“形式化”和“非形式化”方法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探讨。[2](P105)此后,江怡[3](P1~9)梳理了语言哲学从语形到语义再到语用的发展过程,崔凤娟[4](P67~72)的《语用学的哲学维度》一文梳理了伴随语用学诞生、发展的主要哲学思想,特别是符号行为哲学、日常语言哲学,以及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的语用学思想。本文将从哲学的语言转向谈起,从“元语言”,即“自然语言”,在语言哲学中的地位以及人在语言哲学中的位置入手,探寻语用学的源起。
一、“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之对博
(一)哲学的语言转向
语言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有从哲学角度对语言进行的思考、研究是为广义语言哲学;在分析哲学框架中产生,将语言作为研究对象,以建立数学、数理逻辑式的精密科学和揭示语言外人的世界为目的研究是为狭义的语言哲学。[5](P43)人们普遍认为,本体论是古代哲学的中心,认识论是近代哲学的中心,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研究发生了语言转向。哲学家们发现对于存在和认识的研究的关键在于对语言意义的洞悉,正如阿佩尔的说法:“哲学归根结底是对语言的思考。”[6](P13)无论是英美分析哲学,还是欧洲大陆哲学,都从各自的哲学立场强调语言哲学的研究。[7](P2)
20世纪初数理逻辑的迅速发展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哲学的语言转向的动力。语言转向的发动者弗雷格(G.Frege) 、罗素(B.Russell) 和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 都是数理逻辑学家,他们都是借助于数理逻辑方法进行推理,设计使用“人工语言”,借以排除自然语言中修辞类的内容以及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逻辑的主要目标是论证形式化,而哲学的语言转向动力之一就是对哲学问题分析的形式化程度的不足感。
(二)作为哲学语言的人工语言
1.形式化的人工语言
在中世纪,逻辑学和语法学是完全纠合在一起的。[6](P22)句法比语词意义容易形式化,所以,逻辑学从一开始就与语法学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新逻辑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以数学为基础,因此,“数理逻辑”是现代逻辑的本质。语言哲学正是在现代逻辑学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作为从数理逻辑起家的语言哲学家,费雷格的论旨同样充沛着对世界和语言的形式化。罗素的“逻辑原子论提供了一个语言和世界同构对应的模式”。[8](P57)
弗雷格和罗素均认为自然语言有着两个主要缺陷:(1)自然语言有含糊性和歧义性,认为日常语言词义含混,逻辑混乱,因而它不能成为表达思想的完善工具;(2)自然语言不清晰,它的表面语法形式掩盖了它的真正结构,即作为形式的逻辑结构。[2](P102)在弗雷格和罗素思想的基础上,维特根斯坦前期提出了一种精密演算、以分析和解释为研究方法的人工语言哲学。人工语言学派认为日常语言本身混乱不堪,主张抛弃自然语言,仿照数理逻辑另创一套理想的人工形式语言代替日常语言, 以根本消除科学、哲学表述中的含混和歧义。[9](P15)在这种语言中,句法均遵循数理逻辑而严谨地构成。从意义的角度来说,人工派主张“真值意义论”,“人工派的‘真值’立场是和他们要用数理逻辑来对语言进行精密的形式化研究的主张相一致的”。[9](P15)
2. 语言与世界
从费雷格(1892)的《论意义与指称》(On Sense and Nominatum),到罗素(1905)的《论指称》(On Denoting),再到斯特劳森(1950)的《论指称》(On Referring), 无一不是在追寻和探索语言与世界的对应。
海德格尔强调逻各斯、语言和存在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语言就是存在的住所。[7](P28)“语言是存在的住所”正是语言哲学所揭示的语用与世界的关系。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建构。“我的世界就是我的语言的世界”是语言与世界关系最核心的表述,也是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集合。在他的哲学观念里,“命题是事实的逻辑图像”,由命题而成就的语言就是我们的世界。由此可见,前期维特根斯坦关心的其实并不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而是语言自身的逻辑构造问题:由于语言与实在之间具有同构关系,因此研究语言也就是研究实在。[3](P4)
(三)自然语言的哲学回归
逻辑主义在早期语言哲学中占据了中心地位,此后也一直是语言哲学中的一条主线,[6](P24)但逻辑语言,或者“人工语言”,终究是人为定义的、高度形式化的、两极化的表现世界的手段,其中缺乏人的情愫、未能描述人际互动中模糊的边缘地带。
1.日常语言学派
日常语言学派也称语言分析学派或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可见,语言分析是这一学派的重点。其实,逻辑语言学派同样重视语言分析,只不过逻辑语言学派所进行的语言分析,其分析介质为逻辑符号,以数理逻辑为手段,“往往忽视自然语言实际用法中的微妙的但并非不重要的意义区别”。[6](P194)日常语言学派认为逻辑语言学派并没有给出日常语言中任何表达式的逻辑,因为“日常语言本来就没有这种精确的逻辑”。[10]日常语言经常出现歧义、含混和混乱,这一点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并不否认,但他们认为,日常语言中出现的问题要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分析来解决,即以自然语言作为哲学问题分析的元语言。可以说,日常语言学派的语言分析是逻辑语言学派形式极化的必然反转,是对于其过度形式化而致使研究内容缺失的补充,也是在语言研究过程中的人类的自我回归。
2.自然语言是哲学的元语言
哲学与逻辑的并行致使哲学家需要一种高度精确的语言,弗雷格、罗素以及前期的维特根斯坦,都希望有一种符合逻辑的语言系统表述和分析哲学命题,以避免自然语言的“两个主要缺陷(含糊性和歧义性与不清晰性)”。[2](P102)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摩尔、赖尔、奥斯汀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批评逻辑人工语言学派,认为他们忽视了语言中包含的很多重要的逻辑差别,径自把自创的逻辑格式套用在自然语言上,从而他们的语言分析只不过得到了他们自己一开始放进语言里的东西。[6](P194)显而易见,自然语言是日常生活、工作、思考的语言,它本身就是完善的。
因此,日常语言学派之于自然语言的元语言哲学转向是必要的、必然的。这是因为在人工语言的设计和兴起以前,语言分析的介质从来都是自然语言――自然语言是哲学思考的初始语言。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的对攻,就孰为初始的问题而言,稍加思考便可得知:人工语言作为被人赋予特殊意义的符号,其特殊意义是人通过自然语言赋予的,并需要自然语言作为介质进行解释、说明以及传播;反之,人工语言则无法作为通用语言进行解释自然语言。这是其一。其二,哲学是什么?哲学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思维活动,是对世界的探知活动,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活动,是对所有科学的基础的探求,同时也是探求世界和科学的方法论。哲学是客观的、是形而上的,归根结底是一种以自然语言为依托的一种活动。无论是对世界的探知,还是对所有科学基础的探求,还是一种方法论,哲学的活动实施不可能依赖人工语言,究其根本,哲学活动是依赖于自然语言进行的,因为人工语言的定义介质终归是自然语言。人工语言如意欲流通而成为非某(些)人的私有语言,亦更是无法独立于自然语言的传播要通过自然语言来传递。因此,自然语言是“我们由之出发的最初之言”,[6](P205)而哲学的语言最终只能回归到自然语言。毕竟,“语言哲学的任务不仅仅是揭示外在物理世界,而应该揭示人及人的世界,后者包括外在物理世界、人的内在世界和主观创造世界”。[11](P4)
3.人的哲学地位回归
“当我们学习语言,我们便是在不断地接近一些人所谓的‘人类的本质’,它是人脑的显著特性,是人类独有的,是与作为个体和社会的人在任何关键阶段不可分割的”。[12]当语言成为人独具的特征,语言便无法脱离人而独自同构世界,因为人是语言无法摆脱的介质,更是它发挥任何作用的主控者。日常语言才是作为分析和描述的实质性的介质,因为人具有“意向性”,因此人使用的语言同样具有“意向性”。可以说,语言即便与世界具有同构性,语言的启动装置仍然是“人”。
赛尔(J.R.Searle)是当今世界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是日常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奥斯汀(J.L.Austin)的学生。赛尔的心灵哲学、语言哲学为哲学的语言回归至“日常语言”进行了有力有据的论证。
第一,语言的意向性。意向性是为许多心理状态和事件所具有的这样一种性质,即这些心理状态或事件通过它而指向(direct at)或关于或涉及世界上的对象和事态。[13](P1)人的心灵的意向直接导致其语言对世界的组构,如果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从未遇过心地邪恶的人,那么在他的世界里,就没有诸如“邪恶”这样的语言,即便在他的世界里突然出现“邪恶”,他也无法找出相应的语言去对应这种非其意向的世界。赛尔列出了一些表示意向状态的例子,如“信念、害怕、希望……热望、消遣和失望”。[13](P4)意向性是语言的重要特征,因此,当哲学遇到“语言”,也同时遇到了“人”。
第二,语言的可表达性。任何意旨的内容都可以表达的原则,赛尔称之为“可表达性原则”。[14](P19)正如语言的意向性源于人的心灵的意向性,人所表达出的话语同样源于人的意旨。在实际上不可能确切地表达自己意旨的情况下,原则上也是可以确切地表达自己意旨的。[14](P19)可见,赛尔对于人与语言的关系中对人的主控地位的认可。
第三,语言的规约性。按照赛尔的观点,语言不仅与意向有关,而且与惯例或规则有关。如同象棋一样,语言涉及惯例问题;不同的人类语言,可以互相转化,可以看作同一潜在规则以不同的惯例实现。[14](P39)孩子刚学说话,会说“吃水”,会说“没怕的”,是掌握了语言规则的大人教会孩子说“喝水”“不怕的”。惯例也好,规则也罢,均为人的意向的产物。有人才有惯例,有人才有规则,因为是人能动地进行规约。
三、语用学的源起
(一)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
《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转变的标识性论著。他在《逻辑哲学论》中主张,语言是世界的一种反映,即他的图像理论。而他在《哲学研究》中则认为语言是一种和其他行为纠织在一起的活动,即“语言游戏说”,这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主要观点。从《逻辑哲学论》到《哲学研究》,从“图像映射论”到“语言游戏论”,维特根斯坦经历了截然的哲学观点的转变,这个转变使他从逻辑中抽离,转而力图通过观察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使用来探究语言的意义问题。可以发现,维特根斯坦已经距离语用学咫尺之遥。《哲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提到了“意义即使用”这个观点。维特根斯坦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15](P28)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的使用比作游戏。他认为,棋类游戏、牌类游戏等一定有某种共同点,维特根斯坦称之为“家族相似”。[15](P42~43)“语言游戏”一词在这里旨在强调:语言的说出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15](P15)各种游戏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语言游戏就是人类的语言方式、行为方式、也是生活方式。语言游戏说从根本上排除从语言与实在的对应中寻求意义的观念,使对语言的分析从语形和语义的层面转向语用层面。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
哲学界对于陈述之言(statement)所做的描述或陈述,一直以来,只有真实或谬误之说。在奥斯汀提出言语行为理论之前,“哲学界一直认为陈述之言应该具有可验证性”,[16](P2)奥斯汀(1962)对哲学界语言研究中的这种一贯的观点提出了怀疑,他认为许多陈述之言只是貌似陈述,而实际上并不是以坦直地叙述或者传递相关事实为目的。据此,奥斯汀早期把句子区分为叙事句和施为句。前者陈述事实,与真值有关;后者通过所说的话语来进行某种行为,并不描述世界,与真值无关,但可以恰当性进行区分。
奥斯汀虽然区分了叙事句和施为句,但“未能找到区别这两类话语的句法形式上的标准”。[17]因而,他进一步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的新言语行为理论,把言语行为区分为三类: (1)叙事行为或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即“说话”这一行为,主要是发出语音、说出单词、句子;(2)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即“在说话这一动作的过程中实施的行为(传达某种目的如: 警告、命令、问候等)”;(3)言后行为( perlocutionary act),即“说话”这一动作所带来的后果。[16](P94~108)在这三层意义中, 言后行为是他的理论的核心。同时,他还强调意义对于现实语境的依赖,离开了具体语境,单纯的意图、意向不可能构成言语行为。言语得当与否不仅依赖于词语的本身意义,更加依赖于在特定的现实语境下的目的和意图。[16](P145)
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奥斯汀不仅把人们日常使用的自然语言作为哲学问题探究的对象,同时使“人”所想要的后果作为意义释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历代哲学家对于语言与世界关系的智慧思考中,终于“人”这一从未脱离但又从未被注意的在语言与世界关系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得到了相应地谙思。他的哲学研究新方法打开了语言学家的语用视野,为词语的意义注入了语境的释义,言语行为理论成为语用学的基础理论之一。可以说,是“人”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中的位置回归,使语用学蛰生。
(三)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然而,奥斯汀所强调的并非“人”,而是人所存在的语境。真正把“人”作为思维和意义建构的主体,置回于他理应存在的位置上的人是哲学家赛尔。
奥斯汀对施事行为的分类,虽缺乏明确的标准,但他的“以言行事”的观点却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赛尔继承并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在奥斯汀的分类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分类,并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赛尔(1976)指出奥斯汀的分类的不足之处,并找出了不同的言语行为相互区别的12个侧面,其中最重要的是: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point),适从向(direction of fit)和所表达的心理状态(expressed psychological state)。赛尔(1969)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许多其他的社会活动一样,“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图的行为”。[14](P16~17)根据赛尔的观点,语言实际上是“人”自行规定的活动,并且是有“人”各自的意图的活动。除表达“人”各自的意图而外,言语行为的“适从向”以及“心理状态”应充分思及“利他”的初衷和心理需求。虽然“思想家们关注的焦点是‘利他’的动机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开始讨论不同动机所产生的行为”,[18](P40~41)虽然此处的“利他”仅限于满足语言听众的心理需求,而无疑,这是语用学源起的心理需要。
(四)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
哲学家格莱斯把意义区分为“直说的内容”和“含蓄的内容”,并认为“隐含而未直白的内容”与行为有关。所谓直说的内容,是指话语的意义只需要进行表层的理解,并不传递意图;含蓄的内容是“用意”,话语的意义不能只能停留在表层去理解,含蓄的内容是传递说话人的意图。例如,“It’s cold here”,字面含义是“冷”,其“含义”可以传递说话人希望听话人关窗、开暖气或希望离开此地等意图。格莱斯认为,说话人发出一个言说具有“含义”或“用意”, 当且只有当说话人发出的言说试图在受话人那里引起某种效果,受话人理解了说话人的意图并使该意图真正地实现。格莱斯认为,在交流过程中,交际者的交流意向是他们之间的一种共识,具有共识是交流成功的重要前基。这说明,在日常语言中,句子的意义并不等于它们的命题内容,以逻辑语言抽象而出的真值与日常话语中的逻辑概念也并不完全对等。例如:“她怀孕并结婚了。”和“她结婚并怀孕了。”两个句子真值条件相同,但句子含义不同。格莱斯研究的重点在于“非天然意义”, 即非字面意义或字面以外的意义,需要依据语境对话语进行语用分析而得。
格莱斯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交际者在交谈时都遵循着一个原则,即相互配合。交际者在参与交谈时应说符合你所参与交谈的时机和公认目的或方向的话,这就是他提出的言语交际的会话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其中包括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19]。格莱斯认为,交际者在言语互动中须互相合作,合作使交际直接而高效。然而,交际者往往在交际过程中违反某些准则。例如:“A:电话响了。”“B:我在刷牙。”B的回答听起来是所答非所问,违法了关联准则,实则是说明不能去接听电话的原因。此时,B的回答究其合作的层面来看,不合作是表相,而合作才是真象。 因此,违反了某一准则的合作方式,正是非天然意义的潜伏点,这也是推导“会话含义”的语用分析程序。
格莱斯在假设合作原则成立的基础上,效仿康德的量、质、关系和方式这四个哲学范畴,进一步区分了四项基本准则。该哲学理论启动了语用推理模式,扩大了人类语言的“意义”的范畴,进一步巩固了元语言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为语用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哲学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再转向语言从而研究语言的意义以及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哲学一直都在不断地追寻真理。随着奥斯汀、赛尔和格莱斯等哲学家对语言意义的不停探寻,“人”的意向因素回归哲学,语用的语义成为哲学于语义新的中心。语义的语境化、语义的意向性变成语义的真理所在,并催生了语用学。
本文对语用学的哲学源生背景进行了梳理,发现哲学在其发展进程中,在语言与世界关系的探讨过程中,“人”的因素有着由缺位到归位的过程。语用学的蛰生主要源于“人”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中的位置回归。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奥斯汀的“以言行事”以及塞尔继“以言行事”之后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格莱斯的合作原则理论,语言哲学最终成为一种在哲学界可以独树一帜的学科、并独立于语言学的哲学理论, 进而直接导致了语用学的诞生。
[参考文献]
[1]陈思清.语言哲学及其对语言学的贡献[J].现代外语,1991,(1).
[2]俞东明.语用学的哲学基础说略[J].浙江大学学报,1998,(2).
[3]江怡.当代语言哲学研究:从语形到语义再到语用[J].外语学刊,2007,(3).
[4]崔凤娟,苗兴伟.语用学的哲学维度[J]. 外语学刊, 2007,(4).
[5]李洪儒.试论语词层级上的说话人形象――语言哲学系列探索之一[J].外语学刊,2005,(5).
[6]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涂纪亮.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8]徐友渔. 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M]. 北京: 三联书店,1996.
[9]姜孟.关于语用学缘起的三个疑问[J].山东外语教学,2005,(2).
[10]Strawson, P. F (1950).On Referring.In Martinich, A.P.(e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3rd edition)[M].Oxford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1]李洪儒.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之路――语言哲学理论建构之一[J].外语学刊,2011,(6).
[12]Chomsky, N. Language and Mind[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3]Searle, J.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M].刘叶涛,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14]Searle, J.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15]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涂纪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6]Austin, J. L.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M]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7]何兆雄.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18]周纯.利他的文化渊源及其概念界定[J].东疆学刊,2012,(4).
[19]Grice, H. P.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In Martinich,A.P.(ed),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3rd edition)[M]. Oxford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语言哲学观论文第9篇
中世纪语法学中的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对后来语言哲学中的一些论题有深刻的影响。“柏拉图”这样的名词指代的是个体,算是专名,而“人”这样的名词则指称的是类或共相,可以称之为通名。唯名论者与实在论者都承认专名所指代的殊相或个别物是独立于心灵存在的,具有实在性———我通过“柏拉图”这个名字来提及这位大哲,可是他的存在是客观的,并不依赖于我的思想或心灵对他的指向。他们的分歧就在于通名所指称的共性是否也是独立的存在,唯名论者持否定的态度而实在论者则相反。实在论分成极端与温和两派。极端的实在论认为“共相不仅存在在于心灵之外,而且也与个别物分离而存在于个别物之外”[3]41。按照这种观点,“水果”这种共相不但独立于我们的思想,而且也独立于苹果、香蕉、梨这些具体的水果而存在;而温和的实在论在坚持共相独立于心灵的同时承认它们必须存在于个别物之中。对实在论作出过比较全面批判的唯名论者是阿伯拉尔,他的中心论点是:由于共相是可以表达众多事物的东西,因此共相本身不能是事物,不能像事物一般独立存在,因为一个事物是不能用来表达其它众多事物的,只有名词可以。所以,共相归根到底应该是名词,是普通的词项。另一个比较著名的唯名论者是逻辑学家奥卡姆,他提出过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原则,即“没有必要,勿增实体”。奥卡姆认为,知识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逻辑自明的,可以通过分析词项的关系来判断真假,例如,就命题“香蕉是一种水果”而言,我们只要分析“香蕉”和“水果”这两个词的关系就可以判断这个命题为真;另一类是由经验证明的,即比如通过将命题与外部经验事实对照来判断真假,如“火星上有水”。根据这种知识论,“剃刀”原则对实在论的批判可以总结为:无论是出自逻辑的理由还是经验的理由,都没有必要为了解释普遍概念的性质而在个别事物之外设立与普遍概念对应的实体或实在,所谓共相仅仅是具有意向性的词语或符号。
二、近代哲学: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
近代哲学,如前所述,是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在这个时期哲学家被分成英国的经验主义与欧洲大陆的唯理主义,但他们都对语言与思想的关系作出精辟的论述。经验主义哲学家培根在近代哲学中较早讨论语言。他提出在人脑中存在四种假象妨碍人们的认识活动,而其中最难消除的就是由语言误用而造成的“市场假象”。他说:“市场假象是四类假象中最麻烦的一个,它是通过文字和名称的联盟而爬入理解力之中的。人们相信自己的理性管理着文字,但同样真实的是文字亦反作用于理解力。”[5]30培根区别两种可能造成错误认识的语言误用:一是名称无所指称,例如“快乐”“消极”等;二是错误使用名称导致的语义混乱,例如“现象”“本质”“普遍性”这样的概念都常因定义不当而给认识与沟通平添阻碍。应该说,把语言的误用看作是错误认识与无谓争论的源头正是现代分析哲学的出发点。洛克同样对语言的缺陷做出了批判,他首先提出了意义的观念论,认为词指示的是观念而不是事物。“语言所以有表示作用,是由于人们随意赋予它们一种意义,是由于人们随便把一个字当做一个观念的标记。”[6]386接着他指出了语言在表达观念时的主要缺陷以及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所犯的错误:语言自身的缺陷表现在意义混乱,但原因并不在于文字而在于文字所表达的观念;当文字所表示的观念过于复杂,与日常生活联系不多或缺乏准确定义的标准时,语言就会和观念脱节,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哲学的论理词中,因而洛克强调表达观念的语言应符合人们的日常用法。这种思想后来在日常语言学派中得到系统的发展。唯理阵营中对语言转向的发生做出最大贡献的当属莱布尼茨。首先,他在与洛克的论战中提出关于词语指称的一些观点,他同意词语是用来指代观念,但认为观念不一定是外物的反映,观念与外在事物之间存在不对称性。其次,莱布尼茨是最早提出有必要建设人工语言的人,他认为一旦创造出这种语言,人与人之间许多争论就可以像做数学题被脉络清晰地解决,这种设想被看作是“现代物理逻辑以及维也纳学派提出的统一科学思想的雏形”[3]47。语言转向的先行者弗雷格便是这种思想的后继者之一。另外,莱布尼茨明确区分了事实真理和理论真理,提出事实真理是偶然的,来源于经验,而理论真理是必然的,由逻辑或词语的定义决定。这种划分后来被康德发展为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区分,其意义在于“把理性、逻辑、必然性等问题与经验、事实、偶然等问题区分完全放到了语言表达的范围内考察”[3]47。五、康德:分析与综合的两分康德是近代哲学对语言哲学各流派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他为人类理性的范围划定了界限,并对形而上学是否能够成为科学的问题进行了深度探索,引发了一场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甚至有学者指出,现代哲学基本上都是对康德哲学不同反应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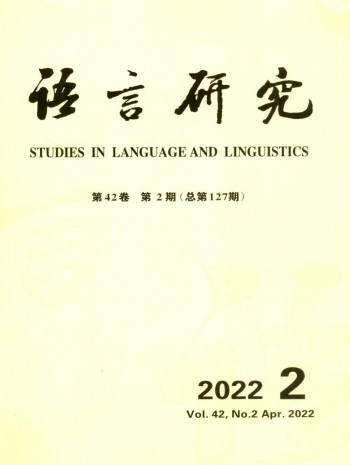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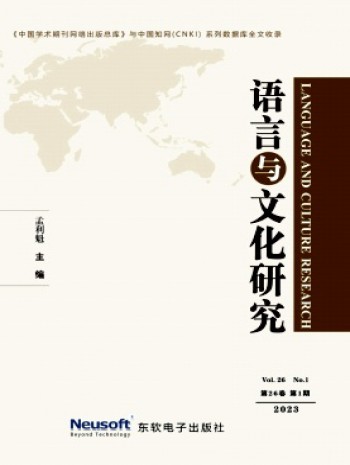


 服务严谨可靠
服务严谨可靠 7×16小时在线支持
7×16小时在线支持 支付宝特邀商家
支付宝特邀商家 不满意退款
不满意退款 400-808-1701
400-808-1701